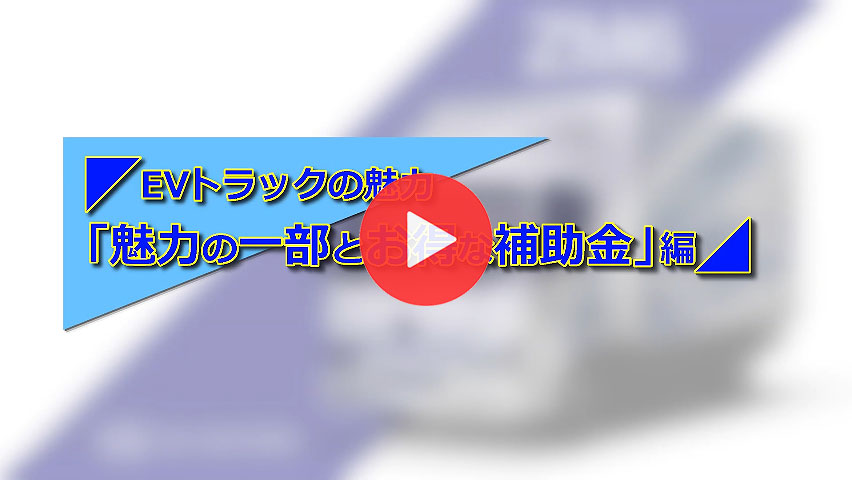林文月汉译日本古典文学作品《枕草子》,修订版序云:“关于散文行笔之间时时出现的和歌,周氏倒是自创三行形式的白话诗以译出;这与丰氏译《源氏物语》用五言绝句或七言二句迥异,反而与我采三行楚歌体之译法较为接近。”
与汉诗相对,日本固有的诗歌叫和歌,它本来有多种样式,但后来唯短歌发展起来,以至于和歌就是指短歌。其定型为五、七、五、七、七,计三十一文字(假名)连缀而成,也就是五行。周氏作人和林氏文月译作三行,与丰氏子恺译《源氏物语》用五言绝句或七言二句一样,都属于译者的任意为之,并没有道理可言。林氏举例:
周译:如果我知道你是听子规啼声去了,/我即便是不能同行,/也让我的心随你们去吧。(另一个版本有所不同:听说你是听子规啼声去了,/[我虽是不能同行,]/请你把我的心带了去吧。)
林译:子规啼兮卿往寻,/早知雅兴浓若此,/愿得相随兮托吾心。(序中误为记吾心,意思就不大通了)
周作人的翻译能让人读个明白,但即便分成三行,恐怕也算不上诗。林文月仿古,所谓楚歌体,最显眼的是兮字。偏巧划拉微信,听一墨家文化探索男说他读了一万多根竹简,有一大发现:兮不发音,不妨去掉,例如“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把虚词统统去掉,这么一节俭,离骚变成六言诗。忍俊之余,不禁想到墨子曰:“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墨家不懂诗。兮是楚辞这种诗的特征之一,具有多重功能。首先是“语于此少驻也”,即句读的作用,因之构成特殊的节奏,并表达咏叹。短歌也有相当于兮的字(假名),叫切字。虽然俳句起劲儿造短歌的反,却终归流淌着短歌的血脉,也使用切字,而且更上心。
例如芭蕉的“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文艺评论家山本健吉说它“自然地打开了闲寂的境地”。此作是俳句最正规的格式,“や”就是切字。14世纪以连歌为业的连歌师救济把“や”、“かな”、“けり”等定为十八切字。芭蕉爱用“や”,据说他上千首俳句中将近二百首用“や”作切字。
俳句比短歌又少了七七,只剩下十七文字(假名)。因为短,俳句的表现手法是“不叙述”。用语言构成,却不能用语言说明,这是俳句的追求,才成其为俳句。只描写景物,少用动词或形容词直接说明感情或状况,更多的、莫须有的意思让读者去想象。好似削足适履,说不定也就炼成暧昧令人难以捉摸的国民性。俳句的定型用五七五的节奏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断叙述,以免变成一句话,亦即散文化。五七五的节奏切断语意,所以不能用“的”把“蛙跳入”(蛙飛び込む)和“水声”(水の音)紧紧相连。节奏所形成的间歇让读者在此延宕韵律,摇曳心神。
切字的作用也是切断,表面上切断语言,切断语言所具有的逻辑,使散文的语言变成诗的语言。切字比五七五的切断更公然,毅然决然。置于最想强调的词语之后,略作停顿,沉吟一番,把语意裁为两截,转换场景或主体。有人将“古池や”(古池呀)理解为表示场所的“古池に”,好比把“兮”换作“于”,这样,“古池”作为“跳入”的补语,前后连成一气,芭蕉彻头彻尾写了一句话:蛙跳进古池的水声。正因为有“や”充当切字,一个叫长谷川櫂的现代俳人认为,这是芭蕉和弟子们在屋里开句会,蓦地听见了声音,并没有看见蛙跳水的身影,所以古池是芭蕉的想象,是他心中浮现的幻影。“青蛙和水声属于现实世界,而古池是用想象力浮现在心的世界里的,二者的层次不同。”这就像一个倒装句:恍若有一片古池呀,刚才听见蛙跳进去的水声。切字之前是心的世界,之后是现实世界。不过,问题在于水是什么水?芭蕉不知道自家院子里或外有一个老池塘,抑或积水成洼?
切字很重要,但现代有一种讨厌用切字的倾向,因为定规的切字是旧的,使俳句显得陈腐。出于对切字的认识,周作人将其译为“古池呀,——青蛙跳入水里的声音。”不仅译“や”为“呀”,而且加上“,——”,尽可能译出咏叹、间歇以及遐思。若用楚歌体,那就是:古池兮青蛙跳入之水声。
热点视频
热点新闻
 |
2026/2/27 |
|
 |
2026/2/17 |
|
 |
2026/2/16 |
|
 |
2026/1/28 |
|
 |
2026/1/28 |
|
 |
202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