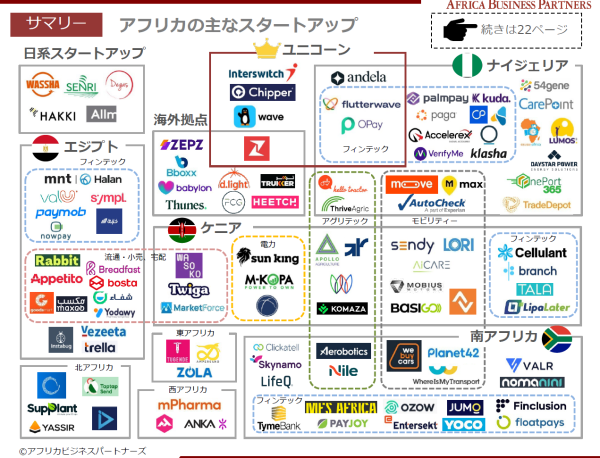
8月14日,日本政府释放信号,拟在第9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上抛出“印度洋与非洲经济圈倡议”,试图以“产学官”联动机制为支点,撬动印度、中东与非洲的经济合作,并强化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叙事。这一动作,既是日本对非洲战略的再调整,也是其试图在中非合作高歌猛进的背景下,以“主动型援助”争夺地区影响力的一次试探。然而,构想虽宏大,其内核仍难掩日本外交的功利底色与战略焦虑。
一、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布局
日本对非合作并非新事。自1993年首创TICAD以来,日本长期以“官方发展援助(ODA)”为工具,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技术转移等方式维系与非洲的联系。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在非洲的“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日本逐渐感受到压力。中国的对外投资自 2010 年代以来激增,远超日本同期规模;日本虽然在发展援助方面积极投入,但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对较小,以软援助为主,欠缺对方产业发展拉动作用。
此次提出的“主动型ODA”概念,正是日本试图突破传统援助模式的尝试。其核心在于从“需求响应”转向“价值输出”:通过主导制定非洲产业扶植、粮食安全、AI人才培养等议题,将日本的技术标准与产业利益嵌入非洲发展框架。而“强化重要矿物供应链”,则直指非洲在锂、钴等关键矿产领域的资源价值,试图削弱中国在该领域的优势。
这种“主动”背后,是日本对非战略的焦虑升级。一方面,非洲人口将在2050年突破25亿,其市场潜力与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经济停滞、人口老龄化加剧,迫切需要外部市场消化过剩产能、获取资源支撑。将非洲纳入“印度洋经济圈”,本质上是日本试图以地理概念重构经济版图,为自身经济寻找新增长极。
二、技术优势难掩地缘博弈底色
日本在制造业、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方面的技术累积,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切实差异化选择。例如,在农业领域,日本通过灌溉技术培训与NERICA稻种推广显著提升农产效率,符合非洲农村对低成本、可持续生产方式的需求;在能源与环境方面,日本也是非洲最重要的双边能源援助来源国之一。与此同时,针对非洲数字化能力建设的系列人力资源项目——尤其在TICAD与JICA主导下,培养“连接日本和非洲”的人才——为未来AI及数字经济合作打下了基础。如果这些计划进入实地推广阶段,有望在缓解人才短缺和强化南南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然而,构想的可行性存疑。其一,资金缺口是硬约束。日本对非援助长期依赖政府预算,而近年来其财政赤字高企。相比之下,中国通过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机构,为非洲项目提供了更具弹性的融资方案。日本若想在非洲大规模布局,仅靠政府拨款显然力不从心。
其二,产业协同难度大。倡议虽提出“产学官”机制,但日本企业对非投资长期低迷。METI数据显示,2021 年日本在非洲的对外投资余额仅约 57 亿美元,不到英国同期投资余额的十分之一。同时,投资回报率问题也成为一大障碍,截至 2021 年,相关投资项目仅获得约 2.1% 的净利润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限制了日本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日本将经济合作与地缘政治捆绑。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到“强化供应链安全”,日本试图将非洲拉入对华遏制阵营的意图明显。但非洲国家普遍奉行“不结盟”外交,其核心诉求是发展而非选边站队。日本若将经济援助政治化,反而可能削弱非洲对其的信任。
三、发展导向是关键
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始终以“真实亲诚”为底色。从蒙内铁路到亚吉铁路,从光伏电站到5G基站,中国项目聚焦非洲最迫切的基建与产业需求,创造了近50万个就业岗位,培训了16万名技术人才。这种“授人以渔”的模式,与日本“技术输出+资源回馈”的路径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的新构想若想真正落地,需回答三个问题:其一,能否超越“零和博弈”思维,以开放态度与中国在非洲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其二,能否将技术优势转化为非洲可负担、可复制的解决方案,而非单纯输出日本标准?其三,能否尊重非洲自主权,避免将经济合作异化为地缘工具?
日本提出“印度洋与非洲经济圈倡议”,既是其经济外溢的尝试,也是地缘博弈的投射。但历史经验表明,非洲大陆的发展,从来不需要“教师爷”,而需要真诚的合作伙伴。日本若想在非洲赢得未来,需少一些算计,多一些诚意;少一些构想,多一些行动。毕竟,非洲需要的不是新的“经济圈”,而是能真正改变命运的“发展圈”。
热点视频
热点新闻
 |
2025/6/30 |
|
 |
2025/6/30 |
|
 |
2025/6/10 |
|
 |
2025/6/10 |
|
 |
2025/6/4 |
|
 |
2025/5/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