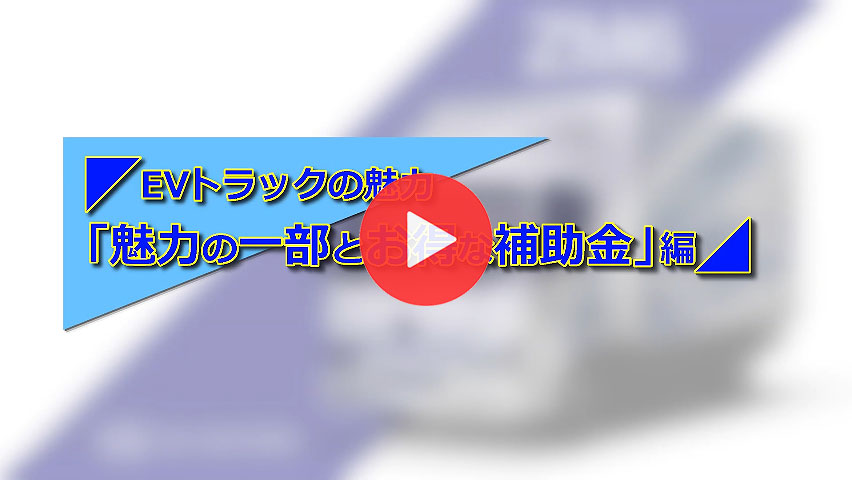(谷美娟(右)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站在熊本地方法院门前,向日本民众说明中国研修生的生活真相)
在熊本县天草市一栋40多年前建造的简陋木楼里,窄小房屋的窗户上挂着一块破旧的毛巾,就算是窗帘了。除此以外,屋内仅有一台小电视、矮桌和铁架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家什。对于3位20岁出头的中国姑娘来说,这种住所显然过于寒酸了,但居住者之一的谷美娟(20岁)则自嘲地说:“与劳动现场相比,这里就是我们的天堂。”
2006年4月,18岁的谷美娟以研修生的身份来到日本。去年8月以前,她一直住在熊本县天草市一家服装公司的宿舍里,屋内全部是拥挤的上下铺,极为有限的空间里硬是被安排了12位来自中国的员工居住。由于洗澡间过于狭小,大家只能一个挨一个地轮换洗浴,而被允许外出购物的机会更是每两个星期只有一次。
即使这样窘困的日子也难以为继。去年9月,谷美娟所在的服装公司倒闭后,她们又被安排到另一处临时宿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她和5位伙伴只穿着随身的简单衣物便匆忙逃离虎口。虽然连许多生活必需品都来不及拿,但她还是把一个笔记本像宝贝一样带了出来,因为那上面有这一年零五个月期间详细的出勤记录:
“8月3日(星期四)8点半-23点;
4日(星期五)8点時半-24点;
5日(星期六)8点半-1点;
6日(星期日)9点半-18点半……”。
她每天下班的时间大都在晚上10点以后,每月只有一到两天的休息,每月的工资则仅有6万日元。如果按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她每小时的报酬只有250日元,还不到熊本县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620日元的一半。
谷美娟出身于中国青岛的一个农民家庭,初中毕业后在当地服装厂工作。她听从日本工作回乡的朋友介绍,在日本工作“收入很高”、“宿舍是双人间标准”、“有的人回国后都盖房子了”等等。在这些动听的诱惑下,谷美娟决心到日本闯一闯。但是,对于刚参加工作不久,月收入仅有1000多元的农村姑娘来说,劳务中介公司4万元的手续费无疑是一个天价。在亲戚和朋友帮助东拼西凑筹足这笔巨款后,她终于从青岛登上开往日本的轮船。
然而,双脚刚刚在山口县下关港踏上日本的土地,令她意外并觉得蹊跷的事就发生了。来接他们的日本公司的老板,一见面就收缴了她们的印章和护照。其后,在乘车抵达天草市的当天,她就被迫惊魂不定地从下午6点工作到晚上九9点。
当时一起到熊本工作的还有6名日本人以及其12名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研修生。这家服装公司从日本某大型高级内衣制造商处承接定单,然后进行缝纫加工,中国员工5人一组,每天必须完成700件的指定工作量,这个标准在日后逐步提高到每天800件甚至1000件。如果稍微出现质量问题,产品就会被日本员工扔回来返工。
收工晚的时候要工作到凌晨3点,深夜回到宿舍后还要和疲惫不堪的同事们分头准备当天的饭食和次日的午饭。
“耳朵里整天回响着缝纫机的噪音,令人寝食难安”,同事们一个接一个地得了失眠症,谷美娟也开始莫名其妙地几乎每天流鼻血。为了谋求合理的休息日,全体中国研修生曾举行过两天的罢工,正当抗争的结果却导致带头“闹事”的中国实习生被強制送回国内。
谷美娟常常听到公司负责人这样讲:“如果你们的工资和日本人相同,我们就没有必要使用中国人。”这番冰冷无情的话语,让她的心灵和自尊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
去年12月,谷美娟和她的两位同事在熊本县天草市当地一家工会组织的支持下,以追讨工资和加班费等名义对该公司和一家派遣工会提起诉讼。今年3月14日,在熊本地方法院门前,谷美娟终于勇敢地拿起了为自己维权的话筒,在街头向日本人诉说中国研修生的生活真相!
直到最近。谷美娟才知道在日本让研修生加班、强迫实习生以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劳动的行为都是被明令禁止的,“那日本公司和派遣工会为什么事先都不告诉我们呢?”
其实,谷美娟也不是开始就想诉诸法庭的。她曾经找到熊本县劳动标准监督署,那里也给双方做了调解。但是,公司的老板称:“以前我们所雇佣的中国员工都生活得很愉快”,摆出一副否认的姿态。结果,谷美娟不得不在异国他乡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了。
目前,在日本一些市民团体的帮助下,谷美娟的房租得到免除,家具和食品也可以依靠公积金联谊会得以解决。她耐心说服在电话中不断催促自己回国的亲友,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当然,谷美娟也有她的焦虑,她说:“已经7个月没做事了,没工作可干的日子是最难熬的。”
热点视频
热点新闻
 |
2026/2/16 |
|
 |
2026/1/28 |
|
 |
2026/1/28 |
|
 |
2026/1/5 |
|
 |
2026/1/5 |
|
 |
2025/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