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谷崎润一郎的文学版图中,《黑白》(中国出版集团,2019年1月第一版)始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部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的长篇小说,既是他唯一一部侦探推理题材作品,也是其艺术理念转型期的关键文本。当唯美主义大师执笔凶杀案,当“恶魔主义”哲学渗透推理叙事,这部如今在中国豆瓣评分6.5的作品也呈现出超越类型小说的文学价值——它犹如一面棱镜,将人性的复杂光谱折射在“黑”与“白”的二元对立之间。
这部小说以作家水野的创作困境为起点,构建了一个精妙的叙事嵌套结构。水野在撰写犯罪小说时,不自觉地将现实生活中的熟人儿岛作为受害者原型,甚至因笔误将“儿玉”写成“儿岛”。这种虚实界限的模糊,在谷崎润一郎笔下演变为惊心动魄的命运游戏:当水野发现儿岛真的遭遇不测时,他既可能是被设计陷害的替罪羊,也可能是潜意识中的凶手。这种设定颠覆了传统推理小说的范式——真相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推导,而是成为存在于作者与读者共同想象中的幽灵。
谷崎润一郎巧妙运用了“暴露式叙事”技巧。水野的内心独白不断解构着侦探小说的悬念机制:“恋爱嘛,是一场戏,不编点儿情节可不行”的自我告白,暴露了所有情节都是人为设计的本质。这种元叙事手法,使小说成为对推理类型本身的戏仿与超越。当水野在银座电影院偶遇儿岛的场景反复出现时,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彻底崩塌,读者被迫在记忆的碎片中拼凑真相,却最终发现所有线索都指向人性的混沌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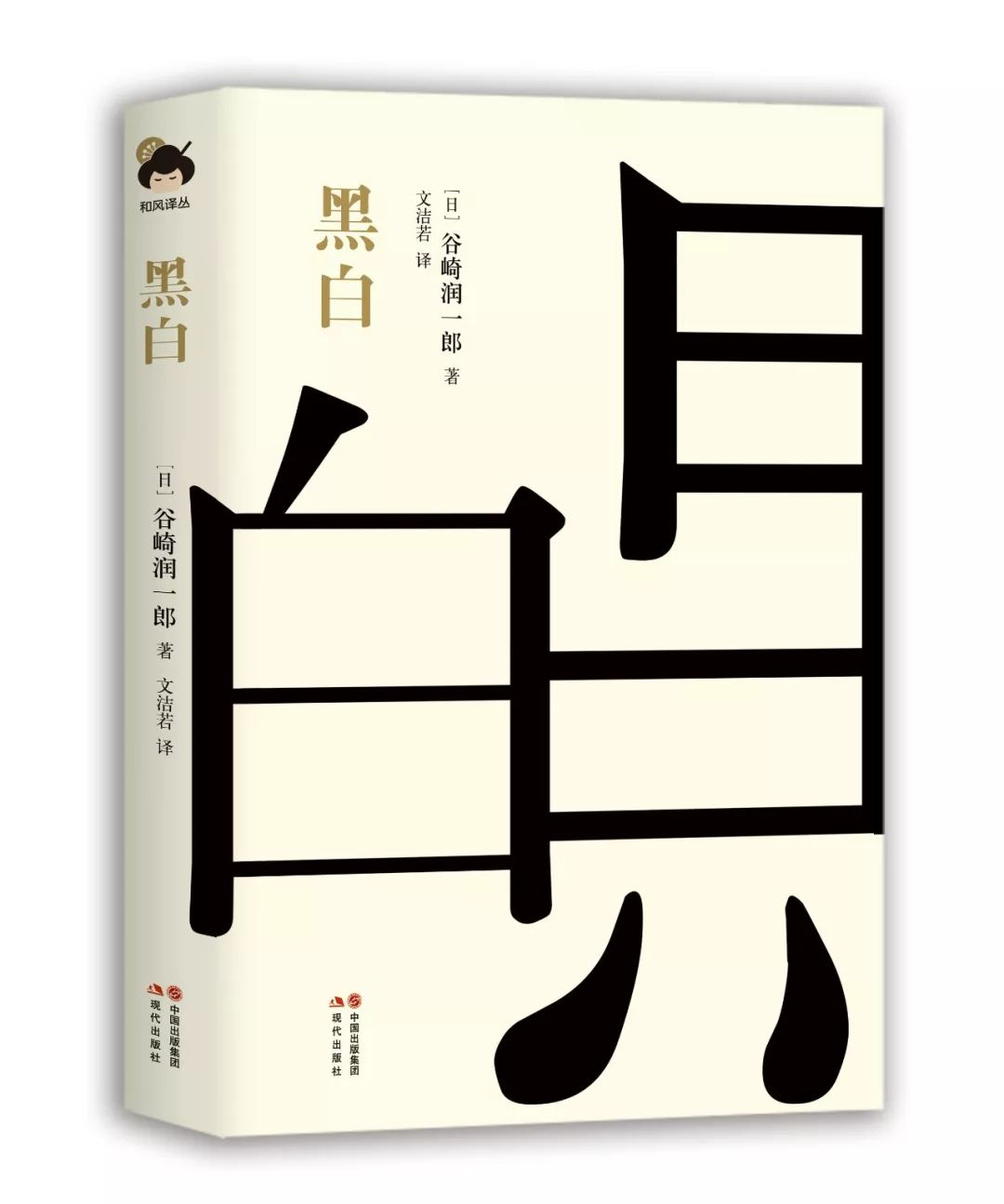
作为自诩的“恶魔主义者”,谷崎润一郎通过水野的形象完成了对传统道德观的解构。水野的颓废哲学具有双重性:他既沉溺于感官享受,用预支稿费满足情欲;又保持着艺术家的清醒,在妓院包厢里观察妓女们“像观察实验室标本”般的冷静。这种矛盾特质在小说高潮部分达到极致——当水野被迫替人顶罪时,他竟在监狱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快感:“文字从笔尖流淌而出,仿佛血液从伤口喷涌”。
谷崎润一郎在此展现了其标志性的暴力美学。儿岛被杀场景的描写充满诗意化的暴力:“月光透过格子窗,在尸体上织出蛛网般的阴影”,这种将死亡美化的倾向,与水野对妓女们“残缺美”的迷恋形成互文。更耐人寻味的是,真正的凶手始终未现真身,这种处理方式将暴力从具体行为升华为存在状态——每个人都是潜在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统一体。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黑白”意象,实则是谷崎润一郎对现代伦理的深刻质疑。水野与妻子美佐子的婚姻危机,本质上是传统道德与个体欲望的冲突。美佐子既有“将丈夫的袜子叠得整整齐齐”的贤妻表象,又暗中与情人保持关系;水野则游走于多个女性之间,却在法庭上坚持“一个男人不该让两个女人为自己流泪”的陈旧信条。这种矛盾揭示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价值真空——当西方理性主义与传统东方伦理激烈碰撞时,个体往往陷入道德相对主义的迷雾。

谷崎润一郎通过水野的案件,构建了一个现代版的“罗生门”。每个相关者都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词:出版社编辑强调水野的才华横溢,妓女们称赞他的慷慨大方,警察则执着于寻找决定性证据。这种多声部叙事,暴露了司法制度的荒诞性——真相不过是大权力者书写的叙事版本。当水野最终选择承担莫须有的罪名时,这个“失败者”的抉择反而成为对体制最辛辣的讽刺。
尽管被归类为推理小说,《黑白》却展现出对类型边界的突破。谷崎润一郎将大量篇幅用于描写水野的情欲经历,这些看似冗余的笔墨实则是揭示人物心理的关键。在妓院包厢里,水野同时与三个妓女调情的场景,不仅展现了他的堕落,更暗示了现代人碎片化的生存状态——每个关系都是浅尝辄止的表演,没有真正的情感连接。
小说对东京都市空间的描写也具有象征意义。银座的霓虹灯与大宫的寂静郊野形成鲜明对比,水野在两者间的穿梭,象征着现代人在文明与野蛮、理性与本能之间的永恒摆荡。当他在监狱里回忆起与儿岛在电影院的最后相遇时,黑暗的影厅成为人性深渊的完美隐喻——每个人都戴着社会角色的面具,在光影交错中隐藏真实面目。

《黑白》的终极价值,在于它拒绝给出简单答案。当水野在狱中开始创作新小说时,这个循环往复的叙事结构暗示着:人性永远在善恶的灰色地带游移,任何道德判断都是片面的。谷崎润一郎通过这部作品,完成了对“恶魔主义”的深层诠释——真正的恶魔不是实施暴力者,而是那些用简单二元对立掩盖世界复杂性的伪善者。
在非黑即白的舆论盛行时代,《黑白》的启示愈发珍贵。它提醒人们:人性从不是单色光谱,每个灵魂都包含着光与暗的永恒博弈。正如谷崎润一郎在小说中借水野之口所说的:“所谓纯洁,不过是未被发现的污点”,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承认,或许才是通往真正道德的起点。(2025年8月11日写于日本千叶丰乐斋)
热点视频
热点新闻
 |
2025/6/30 |
|
 |
2025/6/30 |
|
 |
2025/6/10 |
|
 |
2025/6/10 |
|
 |
2025/6/4 |
|
 |
2025/5/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