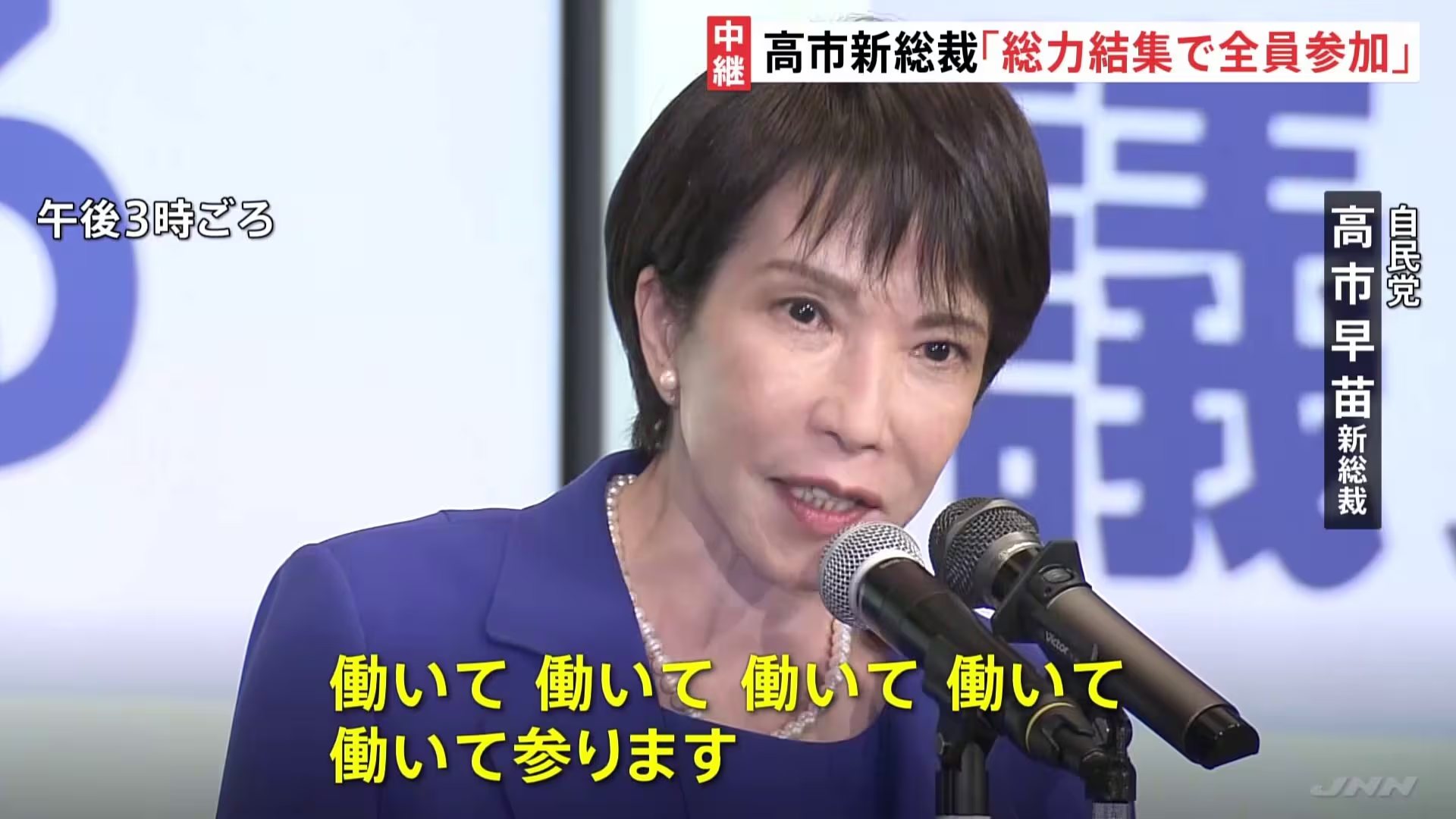三十年代,鲁迅们彷徨日本;八十年代至今,我们也彷徨日本。时代不同了,我们唱的是同一首主题歌吗?彷徨其间,变与不变的是什么?
—— 引自林祁、祁放的随笔《彷徨日本》
采食樱桃之后,穿过升仙峡我们进入温泉——周末“一日游”最后的节目。这温泉有个怪怪的名字,祁放说它的意思是“放置”。好一个“放置”,就这样放置在高高的山野上,放置在这个黄昏的蓝天白云里。
泡在温泉里,正面对着富士山。好哇!千年不变的优美造型,此刻在夕晖的爱抚下,每一丝银发都熠熠闪耀。富士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何况非英雄的我和祁放了。而我们一折腰便诗情大发起来。
我说,这里的天准是泡过温泉,才透明得像蓝宝石,这里的云也准是泡过温泉,才柔美得像少女的微笑;她说,富士山此刻就泡在温泉里,你看她氤氲缭绕,婀娜多姿。如果不说她是祖母形象,那就是少女,银发只是烫出来的现代发型罢。
嘿!蓦然想起,祁放的诗集就题名为“永远的女孩”。永远的是一个古老的情结,一个诗的情结,一个中国情结。女孩还能永远么?
—— 嗯,你问富士山吧。
我望了一眼富士又瞧了瞧祁放。瞧那被温泉泡出来的红扑扑的脸蛋,分明还是二十年前翘着羊角辫的少女模样;分明还是当年参加诗刊社的“青春诗会”时意气奋发的诗人模样。
那是我们共同拥有的青春时代——青春“诗代”啊。那时从“文革荒原”上“崛起”了一代诗群:北岛舒婷们。那诗群里有我,有你,多好啊,我们开始响亮地呼唤爱情,张扬自由。然而,不曾想这“自由”竟成了“资本主义自由化”被横遭批判,祁放在山东省青年中首当其冲。
残阳如血。黄河涛声呜咽。黄河边少女彷徨。娇弱的身姿,沉重的步履。天黑了,风声里是一个“羊肚子手巾”老汉低哑的嗓音:女孩你快回家吧,妈妈着急了……
祁放说这段经历的时候,我眼前浮现的是以上这幅情景。我羡慕祁放生长在黄河边,而我只见过黄河。黄河,你的震撼叫我沉默!祁放说她那时死的心都有了,但她终究没死。也许就因为黄河。因为母亲。
1984年祁放决定东瀛,成了山东省的第2名自费留日的学生。
那时,中国人要走出国门有多么艰难,从祁放纪念母亲的文字中可略见一斑。
“妈妈的眼睛是微眯着的,我怎么使劲,也看不到她真正的表情,不知道她的世界里是不是也下雪?不知道飞机的轰鸣声会不会惊吓到她?妈妈说过她很想坐一次飞机来着……除了坐飞机,妈妈还有什么遗憾?妈妈的遗憾肯定不是坐不坐飞机,妈妈没有看到35寸的彩电,我却许诺给校长,为了让他在放我走的纸上签字;妈妈没有戴过丝绸围巾,我却送给了朋友,为了让他帮我去疏通关系……”
那时,我们只渴望“外面的世界”,只憧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即便“很无奈”也无所畏惧。逃亡的本身就是一种壮举。那时遍体鳞伤的祁放却充满豪情——
我要继续跋涉
带着我的诗行和爱情
秋天,正摇着红叶
向我招手呢
是你在为我唱歌吗
高山、大海
都轰轰地合着节拍
有如不要问我们从哪里来一样,也无须问我们为什么出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动机和契机。有时候理由相当简单。有如祁放,似乎一个“逃”就可以概括。泡在温泉里的我悠悠地想着悠悠地说:那么,你记得到日本第一天的情形吗?
——当然。从来不用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1984年12月18日,我只身一人从北京来东京。早晨出发的时候,北京的天空很蓝很蓝,因为昨天刚下过雪。那时,北京机场还很小,也还没有有引桥的登机口,没有摆渡车,像上火车一样,检完票后,自己要走到登飞机的旋梯口。我穿着一件朱红的毛呢长大衣,一双半高跟的皮棉鞋,兜里装着护照和二叔给的20000和自己在银行兑换的8000日币(那时最多只能换8000日币),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已被扫起堆成雪堆的通道,很想回头看一看送我的亲人,但又怕自己回过头感情不能自己……
我是自己走到飞机的旋梯跟前的,快到飞机跟前的时候脚下一滑,差点摔倒。
飞机在我的眼前越来越大,我的心跳开始加快呼吸也开始急促。天哪,我真的上飞机了,我仰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雪后的无比清新的空气,向左边远远的送行的人们挥了挥手……好像哪个电影上的镜头那样,我的被眼泪模糊的双眼已经看不见爸爸的白发,耳朵也听不见姑姑洪亮嗓音的叮咛,我迷迷蒙蒙地走进机舱找到自己的座位后就开始捂着脸哭了,我突然感到了自己的孤独和无助,毕竟,我去的是我完全陌生和一直被中国唾骂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这算不算冒险,那时,自费留学还是很陌生的单词,而我既不会说一句日语,口袋里也没有学费和生活费,办手续的过程和审批护照的过程已经差不多耗完了我全部的精力和积蓄……加上妈妈前一年刚刚去世,我用自己一个月48元的工资(那时的大学生的工资水平)和积累的稿费才好不容易凑够一张单程的机票。
到东京时,是下午2点左右,出关的时候,无论审查官问我什么,我都说 “谢谢”,因为那时,这是我会的唯一日语。
从机场出来,天上下着小雨,前来接我的外公,身材高大,望着我的目光似乎有些无奈,而我自己对自己的土气的穿着的觉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成田机场到新宿的大巴上,我开始晕车,开始呕吐,我的狼狈让我现在都觉得尴尬,外公什么也没说,递给我一包纸巾,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白这么柔软的纸巾,可惜很快被我用光。
一路上,我什么也没看见,只觉得路很长,很远很远。
到达新宿,已经是傍晚,我在新宿西口下车,抬头望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热泪盈眶……
此刻,泡在温泉里,我已分不清她那脸庞上晶莹的是水是泪,是喜是悲。
祁放感叹着,到日本之后,终于感到了真正的自由,那种突然而来的解放感让自己恍然大悟以前的自己竟然一直未走出那间不透风的铁屋子,尤其是思想。
然而,现实是严峻的。第一份工:洗碗,一天洗上12个小时,早把下辈子的碗都洗完了。
下雪的夜里,寒风吹得小木屋的拉窗直响,夜里躺在四帖的榻榻米上想,日本的“阿怕多”真该叫“阿怕抖”,冷得直发抖。有一天,日语学校的同学——台湾男生买了煤气取暖炉送上门来,比炉子更让她惊喜的,是一套向往已久的三毛的书籍。也许爱情就从寒冷的日子出发了,但男生台湾的父母却在海峡那边竖起一道屏障。要知道那时台湾海峡的“沟堑”并不亚于日本海哟!
台湾男生回台北后请日本友人代为关照祁放。这是一位很绅士的社长,为女士开门挂大衣挪椅子的自然动作,让没见过世面的祁放很是受宠若惊了一阵,活了二十几岁的祁放突然感觉被人尊重被人呵护的滋味,也突然知道了自己是一个女士,而这之前,从中学到下乡到地质勘探队到工农兵学员,她从来没有被周围的任何人当做过女孩儿或女士看过,因为那曾经是消灭女性的时代。
当然不只是祁放,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个乱七八糟的年头,连花布和裙子都被禁止,你还有可能表现和声张女孩儿的美丽和青春吗?
祁放为自己买了一件色彩鲜艳的红裙子,她说她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像花儿一样开放。
祁放在日本遇到了好老师,是东京女子大学的伊藤虎丸先生最先接受了这个把研究论文写成散文的女生,并且不管她哭得鼻涕眼泪一塌糊涂,仍然铁面无私地逼她把论文写成论文的样子才算完事;是东京大学的丸山升先生,又让她在自己身边当研究生,同时参加“东洋文化研究所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活动,让她知道了客观历史的研究是怎么做的。
祁放至今遗憾的是当时放弃了在东京大学读中国文学研究生的机会,而去中央大学大学院学习日本文学,她说,她当时认为自己已经很了解中国的现代文学了,而既然在日本读书,为什么不读自己还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呢?
读自己完全不了解的日本文学是需要勇气的,祁放说她当时最震惊的是日本的学者们对中国的研究深度和研究者的认真态度,而当时的中国却找不到一本介绍日本文化的普通知识读物……
那有什么好遗憾呢?我问,你不是因此多学了一个专业而且也多了解了一个领域了吗?
我遗憾的是因此失去了跟这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们深入探讨现代中国文学的机会,而我学习的日本文学,跟日本同学相比,也只能是一个表皮。当然,是一汪面积大些的浅水湾好,还是一眼深深的井好,是见仁见智的事……祁放说,可我现在哪方面都不过是一湾浅水了。
像这浅浅的温泉?不也很好嘛。我站起身,让毛孔呼吸清凉的空气之后,又将全身泡进暖暖的水里。好爽!
——可不?但那时我心里直发凉。大学院的毕业典礼过后,突然泄了气,突然失去了目标和努力的气力,虽然应老师的邀请开始在大学里教中文,却在连续三节课的“波坡摸佛”之后,躺在榻榻米上大病一场。
祁放开始想家了,于是,就有了拉斯维加斯的只有两个人的浪漫婚礼,就有了出生在旧金山的女儿。
从那时候就开始彷徨了?我晃荡着身边的温泉,问。
—— 嗨,突然找不到北,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站在熙熙攘攘的东京车站的十字路口上,常常想自己是谁,要去哪里?你不可能成为美国人,成为日本人,因为你的文化背景是中国的,而且是打上了那个中国特有的时代烙印。就算换了国籍,也换不了你这个人,你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古人常讲四十而不惑,我们却越来越仿徨、越来越困惑。
那么,什么时候又找着自己了?我掬起温泉往她头上浇。
——从开始做NPO地球文化交流会的理事开始。祁放在十几年里,已经为两国的文化经济交流做了数不清的工作,而且全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
你学雷锋?还是能得到什么表扬或奖励?我开起玩笑。
祁放的眼圈开始发红,幽幽地说,一个说不清楚的情结呀……
为了那块土地,那块曾经养育了却又伤害了她的土地,那块洒满了青春的诗情和眼泪的土地,那块埋葬着母亲和父亲的土地……
——你想过我们死的时候,该埋在哪儿吗?
没想过,我说,你呢?
你看过三文鱼四年一次的大洄游吗?祁放似乎答非所问——
三纹鱼在日本也叫鲑鱼,大多出生在北方的清澈的河流里,刚从卵中孵出的稚鱼会在附近的河里或湖里成长,一年之后便游向大海。尽管大海里充满了危险。四年后,稚鱼已经长大成人,为了留下子孙后代,开始溯流而上,几千里的路程,它们不但要越过无数的坡坎,还要经过被吃掉和被捕获的危险,当它们中的几万分之一总算顺利地回到出生的小河时,几乎都已遍体鳞伤……
遍体鳞伤的三纹鱼在故乡秋天清澈的小河里产卵后,便耗尽了全部的精力和体力,而把尸骸留在那儿,给即将出生的后代留下食物……
祁放似乎在说一个令人回味的寓言。可是,我们不是三纹鱼,我们不必拘泥,我说。
我读过她的《人在远方》,诗云:
无论怎样伸长
青藤般的手臂
我都无法再触摸到
你的温柔
和
你的美丽
母亲啊
喂,你还写诗吗?我几乎是喊着问。
祁放从行李包取出一首新写的诗给我看——
我决定过自己不在你面前哭泣
而且刚才,我们也一直是在笑
却在你拥抱我的那一瞬
全部变成了亮晶晶的眼泪
你的拥抱把我胸中的盒子挤破了
那是装满了感情的盒子
尽管我已经装上了锁,还压上了重重的石块
可是泪水还是瀑布一样
喷涌而出……
诗是只身一人在美国读高中的16岁的女儿写的,那个美丽的女孩儿叫LUCKY。
温泉。夕晖。富士山。
呵,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热点视频
热点新闻
 |
2025/12/25 |
|
 |
2025/12/24 |
|
 |
2025/12/23 |
|
 |
2025/12/17 |
|
 |
2025/10/7 |
|
 |
2025/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