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日关系发展创新的日中友好会馆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日中友好会馆,是中日友好合作的创新,也是范本。自1982年创立以来,日中友好会馆持续为推动中日民间交流、尤其是青少年交流和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请具体介绍一下日中友好会馆的性质、业务及您的主要工作内容。
黄星原:首先,我想借《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平台祝新中国76岁生日快乐!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日中友好会馆(以下简称会馆),是中日友好合作的创新,也是政府推动民间交流的范本。我想补充一句, 会馆还是中日两国的先贤们着眼长远,以大智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先例。如果从“善邻会馆”算起,会馆今年已经有90 年的历史。
说到日中友好会馆的性质,用中日两国政府45 年前决定成立这一机构时的定位来说,就是:由中日双方出资出人共同管理经营,为促进双边经济文化教育等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流而专门设立的“中日两国共同事业”平台。这在全球是首创,在日本也是唯一的特殊存在。
随着中日关系深入发展,会馆的业务范围也从传统的五大支柱,即:文化、教育、环保交流、为中国公派留学生提供居住和生活协助、以及通过日中学院提供语言培训等之外,现在又增加了学者智库交流等新内容,进入“五加N”交流新模式。
日中友好会馆创始负责人是日本政治家、众议院议长古井喜实和中国的廖承志副委员长。我是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从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任上直接转到日中友好会馆工作的。这充分说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民间交流工作,尤其希望会馆作为中日两国共同事业平台,能在疫情严重阻隔人文交流的情况下发挥独特作用。
中国代表的主要责任是,确保会馆管理运营不出问题,确保会馆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宗旨不出偏差。这项工作是在与日方代表协调合作下完成的,对于我来说既新鲜又有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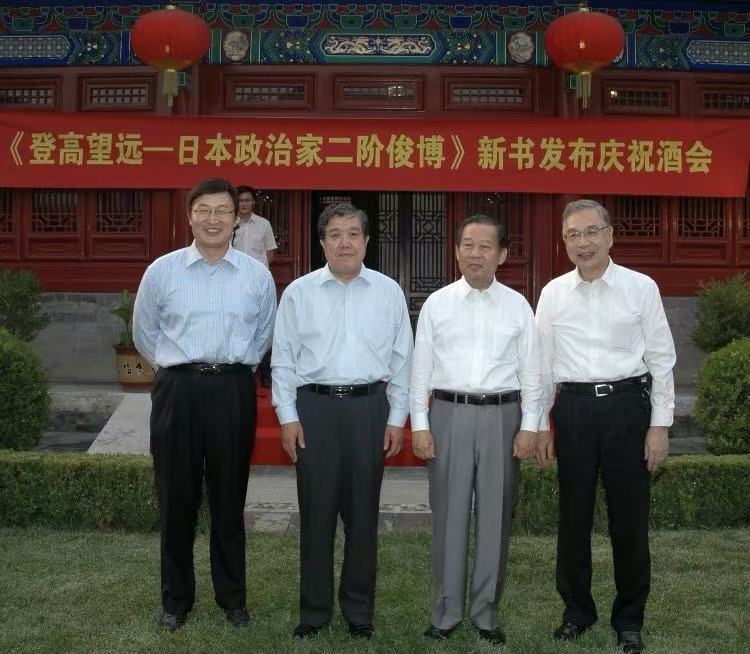
“三进日本”感受中日关系“三个时期”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您本人曾于1989 年至1995 年间在中国驻长崎总领馆和中国驻大阪的总领馆工作,2001 年至2005 年间再次到日本,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如果算上您担任日中友好会馆中国代表理事,真可谓是“三进日本”了。您这三段涉日工作经历,应该说是极具时代代表性。请您从亲身经历为读者讲述这三段历史时期,中日关系的不同发展特点、外交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日本民众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的改变。
黄星原:的确,我很幸运!在日本常驻的三个时期,对于日本以及中日关系来说都非常有代表性。我也因此完成了从日本地方到首都,再从政府外交到民间友好交流的角色转变。
我第一次常驻日本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上半叶,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在长崎、福冈和大阪三个总领馆工作过六年。那时中国正在热火朝天的搞改革开放,渴求引进日本的管理经验与技术;日本经济高度发达,甚至买下整个美国地产的心思都有。那个时期的中日关系可以用“蜜月期”来形容。总领馆的辖区很广,我的工作内容也很繁杂,但乐此不疲。总体印象是:日本民众对华友好,政府内外政策相对宽容。三千名日本青年访华大交流是那个时候搞的,日本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也是那个时候实施的,日中友好会馆也是那个时候建成的。
虽然那时也有右翼反华份子,但成不了气候。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后发现苗头不对,就没有再去第二次。否定历史的日本右翼政客发言引发舆论哗然,结果就怏怏下台了。
我第二次到日本工作是本世纪初,做了六年的中国驻日本使馆新闻发言人。与之前一样每天都很忙碌,不一样的是有了不少担忧。那个时期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日贸易额也突飞猛进。而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发展裹足不前,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当时的中日关系突发事件不断,可以用“摩擦期”形容。总体感觉是:中日经济实力越来越接近,两国国民感情却渐行渐远。当时还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如:右翼车撞中国驻大阪总领馆事件、长崎和平少女像被泼漆事件、日本历史教科书遭篡改事件等等。突发事件一个接一个,可谓是按下葫芦又起瓢。那段时期,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一年又一年,犹如西瓜皮擦屁股——没完没了。我作为使馆新闻发言人到处接受采访,天天阐明立场。我也因此被盯上了,还接到过刀片和不明粉末等特殊“礼物”。

新冠疫情开始不久的2020 年秋天,我第三次来日本工作。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我是作为具有政府背景的民间机构中国代表身份来的。因为做的都是友好交流的事情,日程每天安排的很满,讲话、剪彩、站台等等活动接连不断。快速发展的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失去了三十年”的日本,经济也开始展现韧性和新的活力。经历过高潮与低谷的中日关系,也可以说迎来了“重塑期”。我的总体感觉是,中日间除了邻里关系没有变化,其他的几乎都发生了改变:日本首相又开始走马灯似的轮换了,只是懂战略有远见会平衡的政治家变少了。坚持友好的团体和个人意志还是那么坚定,只是岁数越来越老了。电视上专家学者仍然很活跃,只是调门儿开始一边倒了。中日两国间旧矛盾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现,只是处理腾挪空间变小了。这种变化与百年未有大变局下的大国博弈有关,与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短视错误战略定位有关,也与因焦虑而错位国民心态有关。
好在最近一段时期,由于国际及地区局势的深度演变,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不断恶化的中日关系不符合其国家利益,也不利于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一些理性声音开始出现,认为亚洲经济第一第二的两个重要国家,有责任和义务改善关系,发挥地区大国的引领作用。中日关系最近也因此呈现出改善的良好势头。我注意到,最近双方均表示愿以两国领导人已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按照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双方都强调要积极推动民间尤其是青少年交流,夯实两国民意基础。这给了民间交流,特别是我们会馆大有作为的机会与空间。
充满温情与温度的中日民间交流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关键时刻,您不辞辛劳的奔波于各自类型的交流活动,躬身力行推进中日交流与互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请您为读者讲述一两个,在您所参与的活动中令人感动或难忘的例子。
黄星原:说实话,我这两年年均参加各类交流活动至少在五百场以上。其中既有致辞剪彩等热闹非凡场面,也有对谈研讨等深入交流机会,“曝光率”一点不亚于我做大使和新闻发言人的时期(笑)。今天,我举一个远一点的和一个近一点的两个例子,把我的感受分享给读者。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我来会馆的第二年,当时新冠疫情还相当严重。在年底的一次线上交流活动中,会馆挑选了访问过彼此国家的中学生进行视频交流。几十人通过视频同步互动,对于组织方会馆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交流体验。通过网络把分散在各地的同学聚在一起,时而集中时而分组,一会儿派代表发言一会儿又集体分享,忙得不亦乐乎。
但对于手机电脑不离手的中日两国的孩子们来说,真的是驾轻就熟。他们把之前访问对方国家时的图片资料和美好回忆,通过动漫以及小视频等方式完美表达出来。还把自己访问时学会的对方国家的音乐或者民谣,要么演奏要么演唱分享给其他小伙伴。他们谈到高兴时忘情大笑,说到想念之处会掩面而泣。我作为观摩者,也受现场气氛感染,被孩子们纯情与真心感动得心潮澎湃。
疫情期间,我参加了孩子们数十场线上交流活动,从他们的欢声笑语中感受到了两国青年携手战胜疫情的力量,也看到了中日友好后继有人的希望。正是有会馆这样的民间机构不间断地坚持做民间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流工作,在疫情期间中日间人员往来几乎全面停滞的状况下,架起了一座座人与人、心与心沟通的桥梁。

第二个例子就发生在前不久。中国的一位画家找到我,希望帮忙找一位日本书法家与她一起在会馆举办书画交流展,以书画同框方式体现中日文化同源意义。我通过朋友京都大学张敏教授找到了日本书法界泰斗杭迫柏树老师,没有想到这位92 岁的老先生痛快地答应了下来。不仅提供了优秀展品,还冒着酷暑亲自从京都宇治赶来东京参加开幕式。当这位鹤发童颜的大师西装笔挺地出现在会馆美术馆现场时,来宾们无不为之动容。
杭迫先生的许多作品收藏于日本的博物馆、首相官邸等处,展示在中国驻大阪总领馆接待大厅,并被日本知名服装品牌设计成文创产品以吸引年轻人。老人家向我介绍说,前不久他在安徽省博物馆完成的个展,这是他第90 次访问中国。他对中国的热爱源于东方文化,深于中国书法,结晶于“王羲之书法字典”巨著的完成。这部字典是他从十万字的研究成果中提取出的万字精华,成为了全球研究王羲之的唯一相关参考工具书。我更是从他气势磅礴刚劲有力的行草笔锋里,以及行云如水一气呵成的汉字书法作品中,感受到老人家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和浓浓的中国情。
舆情调查与中日关系的走向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由“言论NPO”和中国外文局共同实施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反感”的比例增至87.7%,创下该调查实施20 年来的最高纪录。在问及“留学、学术交流、文化交流等民间交流活动,对于改善中日关系重要吗?”时,半数以上日本受访者表示重要,但仅有25.4%中国受访者认为重要。您是否赞成这一调查结论?在您看来,症结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如何改变?
黄星原:作为“北京—东京论坛”早期参与者以及“言论NPO”舆论调查问卷设计者之一,我认为这项舆论调查的结果与问题的设计,民调对象与人员结构,和当时的两国关系大环境和小气候都有关联的。政府政策倾向、媒体舆论导向、社会保守思潮、以及突发事件等都会影响到当时的民意调查结果。调查反映的一些苗头和倾向需要警惕和重视,但具体数据仅供参考,不必过于拘泥的。
具体到留学、学术交流、文化交流等民间交流活动对于改善中日关系重要性这一问题上,半数以上日本受访者表示重要,仅有25.4%中国受访者认为重要的结论,我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作为有十四亿人口和诸多邻国的中国来说,受访者可能更相信国家政策对外交关系改善的直接作用。而对于贸易立国的岛国日本来说,受访者大多相信国际交流的重要性。我在“熊猫杯”舆论调查结果分析时发现,日本年轻人只要去过中国或参与过面对面交流的人,对中国印象都很好。有七成以上的年轻人认为日本媒体对改善日中关系没有发挥好作用。在日本,专家学者和民间组织和团体特别活跃,我也因此接到了大量的活动邀请。
二是留学、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等在中国开展的较晚,主要集中于改革开放以后。交流对国家关系和民意的改善影响尚不明显。但在日本,由东向西的交流早在中国隋唐时期就开始了,明治维新后这种交流更是如火如荼。学术和文化交流有政府政策鼓励、有企业资金支持、即成体系又有规模。日中友好会馆的青少年交流和植树造林两个项目,主要是依托于日本政府的两个专项基金支持完成的。关于如何改变近而不亲这一现状?这即是外交课题也是公关难题。这里,我想提三点建议供参考:
第一、如何看待和定位对方非常重要。正确的战略定位是决定中日关系走向的纲,纲举才能目张。把对方确认为威胁还是伙伴,其政策和导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经常在不同场合举以下两个例子:一个是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两国正确的战略定位和政治家的勇气发挥了关键作用,中日关系也因此进入黄金时代,为两国的合作与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第二个例子是1990 年,在西方集体制裁中国的情况下,时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率先访华,使中日关系“蜜月期”得以延续。后来,我们在一次交流中他告诉我,他不后悔当时的做法,认为那符合日本的国家战略利益。今后也是一样,只要双方切实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把战略互惠关系定位贯穿到对彼此外交政策始终,贯彻到涉国家发展利益的方方面面,改变远交近攻、“安美防中”外交政策和安全观,中日关系就会行稳致远。
第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方法仍然有效。历史的实践一再证明,积极推进民间、地方、媒体和智库、特别是青少年交流,是两国关系出现问题时的黏合剂,也是政府沟通渠道堵塞时的第二管道。中日两千多年的交往和邦交正常化五十多年的历史告诉人们,只有遵守四个政治文件的战略约定,珍惜经济互补优势和三千多亿美元贸易额的彼此利益,搞清楚大变局下地缘政治彼此利益需求,不断夯实友善的民意基础,中日关系的大船才不至于在小河沟里翻船。
日本友好会馆今年12 月13 日将推出一个展览,纪念新中国第一个民间代表团访问日本。71 周年前,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女士率团访问日本时,日本的政治环境还相当恶劣。没有想到她抵达日本之后,却受到上万民众自发的夹道欢迎。这不仅为两国雨后春笋般的民间交流开了好头,也为后来两国邦交正常化铺平了道路。我们现在的情况,比那个时候要好的多,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次启动“以民促官”这把万能钥匙呢?
第三、良性循环舆论生态环境不可缺少。我过去长期与媒体打交道,改变因为信息不对称形成的成见,需要政治家的思维改变和破冰勇气,需要媒体人和舆论场的良知良能,也需要老百姓的支持配合。我们经常把政府决策或者政治家的行为、舆论引导或者对突发事件的炒作、以及包括极端情绪在内的民意基础,看作是影响双边关系改善的“循环链”,无论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两国关系的走向。我们注意到,每当中日关系要企稳向好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地受到一些偶发变故或者突发事件的干扰。双方需要共同努力,提高警惕的同时,也要登高望远审时度势,努力提升管控风险化解危机的能力。
日中友好会馆在未来两国关系中的作为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里接连发生的几桩标志性的大事件,中日关系乍暖还寒。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并确认了“构建有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的必要性,现在,首相有可能要换人了,两国领导人之间刚刚出现的良性互动势头会不会变?电影《南京照相馆》和《731》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日本却担心是反日教育。您认为中日高层互访最近还有可能吗?未来的中日关系将如何发展?日中友好会馆作为中日两国的共同事业平台,为开展民间外交做了哪些配合,今后有何工作计划?
黄星原:高层交往对双边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这在中日关系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被充分证明。我从会馆创始会长古井喜实的《日中关系十八年》回忆录里了解到,古井先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是带着三个问题去的:中国共产党能执政多久?中国社会主义是否有特色?中日友好有没有前途?在多次与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交往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稳固,因为有民意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大有作为,因为有自己特色。中日关系未来可期,因为有政策支撑。正因为把握这些原因,古井先生此后毕生投入中日友好事业,在其做日本议会议长期间,积极促成日中友好会馆建立,并且亲自担任首任会长,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承认一个现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三尺冻冰也非一日之暖。越是中日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越可以甄别政治家与政客的水平。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先生不久前受邀出席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活动,本来是很好的展现日本反省侵略历史、珍爱和平的外交互动机会,在日本却遭受指责。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在坚定地维护日本的国家形象和利益,也是在真正地推动中日友好。只是,现在日本像鸠山先生这样有战略高度和思想觉悟的政治家已经不多了。
日中友好会馆作为中日两国的共同事业平台,最近也在积极开展民间外交:1、会馆新任会长、前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在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十多次访问中国,会见中国领导人并与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日中关系交换意见。今年中国国庆节前夕,他还亲自率领日本长野县数十人的青少年艺术交流团访华,在雄安新区与中国孩子们的联袂演出,场面十分感人,2、去年下半年开始,会馆与中国人权基金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共同举办中日关系研讨会,为学者智库交流开辟了新渠道。3、会馆美术馆举办的介绍中国的有关展览和电影节,其中的“古长安作品展”参观人数达万余人,创近40 年新高。4、推动中日青少年交流项目顺利完成。就在中国“9.3”阅兵之际,会馆组织的青少年代表团也在中国参观访问。
旅日侨胞应发挥什么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从您的工作经历来看,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的侧重点有何不同?作为一名中华儿女,旅日侨胞应该做些什么?
黄星原:我从事外交工作已经整整四十年。前35 年,我一直在从事与政府外交相关的工作。最近5 年,是在为促进两国民间友好交流做工作。其实目标没有大的差别,只是异曲同工而已。
严格意义讲,把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分开未必科学。现在的政府外交需要民众的支持与配合,也就是公共外交概念。民间外交也离不开政府政策指导和支持,即是有别于政府外交的另辟蹊径,也是有利于政府外交的有效补充。
就个人经历而言,做政府外交期间,我打交道的对象更多是官员、智库和媒体。工作内容也集中在介绍中国立场主张和原则,特点是交锋交涉的场合多一点。但做民间外交就有了不少变化,除了打交道对象发生变化外,工作内容也有许多不同。深入地方讲中国故事,举办展览传播中国文化,站台、剪彩、甚至品中国菜、喝功夫茶都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我也因此发现,在推动中日友好合作态度方面,民间比政府积极,地方比中央务实,企业比官僚着急,民众比媒体公正。这就给包括日中友好会馆在内的民间友好团体和致力于中日友好合作的仁人志士大有作为的空间。
日中友好会馆的许多工作与在日中国侨胞有关,也得到了同胞们的大力协助和支持,我愿意借此机会表达诚挚的谢意。这支人数过百万的队伍,不仅是中华文明和中国经济奇迹的受益者,也是日本社会发展变化的见证人,更是中日友好合作的桥梁和生力军。
如果一定要给我们在日的同胞提点什么建议的话,我就把10 年前讲给我女儿的话在这里重复一遍:一是坦坦荡荡做遵纪守法规矩人,不给老爸丢脸。二是健健康康做积极向上阳光人,不让老妈担心。三是勤勤恳恳做利国利民接班人,为家乡建设出力。四是扎扎实实做相互理解的搭桥人,给中日友好不断添分。

热点视频
热点新闻
 |
2025/10/7 |
|
 |
2025/10/4 |
|
 |
2025/10/4 |
|
 |
2025/9/6 |
|
 |
2025/9/6 |
|
 |
2025/8/2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