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的长江北岸,暑气尚未蒸腾成云,我站在黄州公园路的古牌坊下,仰头望着“东坡赤壁”四个遒劲大字。这座被苏轼误认作三国古战场的赭红色岩壁,历经千年风雨,早已成为中华文化基因里最鲜活的注脚。当5月广东惠州西湖的烟雨还在我记忆里氤氲,黄州赤壁的江风已裹挟着历史的沉香扑面而来。
沿着林荫小径拾级而上,赤鼻矶的丹霞地貌在暮色中愈发瑰丽。岩壁如凝固的火焰,褶皱里沉淀着长江千万年的奔涌。大清王朝康熙末年黄州知府郭朝祚题写的“东坡赤壁”门联散发着独特的光芒:“客到黄州,或从夏口西来武昌东去;天生赤壁,不过周郎一炬苏子两游。”这副对联恰似时空的枢纽,将三国烽烟与北宋文脉在此交织。

二赋堂前的紫藤垂落如瀑,清人李鸿章题写的匾额下,程之桢楷书《赤壁赋》与李开汉隶《后赤壁赋》分列两侧。指尖抚过木刻上“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凹痕,忽然懂得余秋雨所言“苏轼选择了赤壁,赤壁也成全了苏轼”的深意。那个秋夜,被贬黄州的东坡居士,正是在这江风月色中完成了对命运的突围。
酹江亭的飞檐挑起最后一缕霞光,亭中石碑镌刻着“一樽还酹江月”的苍劲字迹。江面早已不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壮阔,但当暮色中的货轮拉响汽笛,恍惚间竟与千年前的战鼓声重叠。地理的错位在此刻显影——真正的赤壁古战场在百公里外的蒲圻,而这座被苏轼误认的“文赤壁”,却因文学的加持成为永恒的精神地标。
穿过竹影婆娑的甬道,雪堂的茅草屋顶在暮色中若隐若现。元丰三年(1080年)那个雪夜,苏轼带领家人筑屋垦荒,把五十亩故营地化作“东坡雪堂”。堂内塑像定格了文人躬耕的瞬间:竹杖芒鞋,布衣草帽,眉宇间却透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

雪堂西侧的东坡问稼亭,至今陈列着《东坡八首》的拓片。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诗句,见证着士大夫向农人的蜕变。更令人动容的是堂前老井,当地人说井水至今清冽甘甜,仿佛还浸着东坡先生的旷达。
在栖霞楼的凭栏处,遇见几位临摹《景苏园帖》的老人。他们笔下的“大江东去”带着黄州口音的顿挫,让我想起苏轼在《答秦太虚书》中的自述:“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正是这种困顿中的坚守,催生了“一词两赋”的文学巅峰。
二赋堂后的碑廊里,139块苏轼书画石刻早已苏醒过来。其中《寒食帖》的拓片最令人驻足,那些“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笔触,将贬谪生涯的寒凉化作艺术的炽热。清代杨守敬选刻的《景苏园帖》,更是将苏轼的诗文、书信、题跋悉数收录,堪称东坡文化的基因图谱。
石字藏前的香炉青烟袅袅,这个古代焚烧字纸的场所,至今仍保持着对文字的敬畏。明代方孝孺在此留下的“字葬”传统,让我想起苏轼在《石苍舒醉墨堂》中的喟叹:“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但正是这种对文明的执着,让东坡赤壁成为中华文脉的活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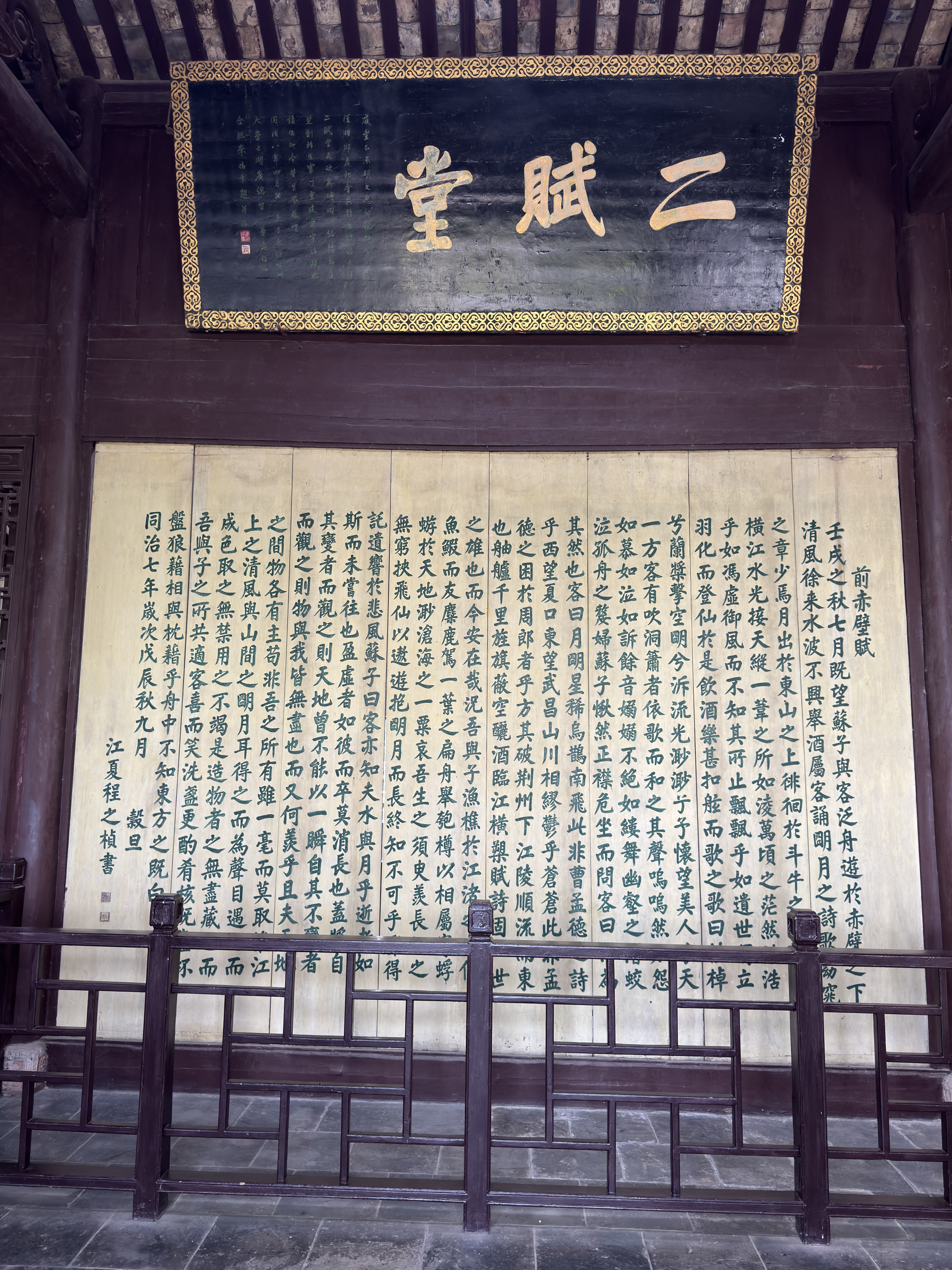
我在问鹤亭遇见一位老人。他指着碑廊尽头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石刻说:“这块碑的‘樯橹’二字,有人考证应为‘强虏’,但东坡先生写的是心中丘壑。”月光透过古柏洒在“人生如梦”的刻痕上,忽然明白:真正的历史从不在故纸堆里,而在这些被时光摩挲得温润的石刻间,在代代相传的诵读声中。
我沿着新修的临江栈道漫步。虽然“卷起千堆雪”的江涛已成追忆,但江风中依然回荡着文明的密码。1998年东坡赤壁被定为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工作人员在栖霞楼地基下发现宋代瓷片,那些碎片上的冰裂纹,恰似中华文明历经劫难却始终不灭的证明。
我还遇见一群研学的中学生。他们用手机拍摄岩壁上的《赤壁赋》刻石,讨论着“物与我皆无尽也”的哲学命题。这让我想起苏轼在黄州完成的不仅是文学突围,更是对生命意义的重构。就像他种下的东坡米,在贫瘠的土地上依然能结出饱满的稻穗。

回望着那被朝霞染红的岩壁,多像被岁月点燃的文明火种。从杜牧的折戟沉沙到苏轼的江月酹酒,从李白的“二龙争战决雌雄”到秋瑾的“挟策寻诗赤壁游”,这座被误认的古战场,早已超越地理坐标,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原乡。
江风送来货轮的汽笛,惊起栖霞楼檐角的铜铃。这声响,与千年前的战鼓、诗人的吟哦、学童的诵读交织成曲,在长江的波涛里生生不息。东坡赤壁教会后人:真正的历史不在考古报告里,而在文明基因的传承中,在每个中国人面对困境时,依然能吟诵“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里。
热点视频
热点新闻
 |
2026/2/12 |
|
 |
2026/1/28 |
|
 |
2026/1/28 |
|
 |
2026/1/5 |
|
 |
2026/1/5 |
|
 |
2025/12/25 |













